-
(一)具有2年以上投資經歷,且滿足以下條件之一:
家庭金融凈資產不低于300萬元;
家庭金融資產不低于500萬元;
近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40萬元。 -
(二)最近1年末凈資產不低于1000萬元的法人單位。
-
(三)金融管理部門視為合格投資者的其他情形。
近期關于加強影子銀行的監管又成了很多人關注的話題,其中明確的一個路徑就是:信托公司應回歸主業,回歸信托“受人之托,代人理財”的功能定位,監管層也在積極推動信托公司業務模式轉型。那么,信托怎樣才算回歸了主業?我們認為,標準的資產證券化才是化解銀行“非標”產品及影子銀行風險的正途,因為如此才符合國務院提出的要優化金融資源配置,用好增量、盤活存量,更有力地支持經濟轉型升級,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理念。簡單梳理信托行業三十多年發展的歷史,就可以看出這一點。
改革開放后的1979年,中國銀行總行率先成立了信托咨詢部。同年,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在北京成立,標志著信托業得以恢復。到1988年,國內信托公司多達745家,雖對當時中國吸引外資、搞活地方經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,但信托公司沒有真正辦成“受人之托、代人理財”的機構,實際成了吸引存款、發放貸款的銀行,帶來了很大的金融風險。為此,從1982年起,為化解和處置金融風險,國家對信托公司進行了5次大的清理整頓,撤并了大量機構。歷次的清理整頓中,信托業都處于停業或者半停業的狀態。
經歷了“推倒重來”式的清理整頓后,信托公司于2004年后又出現了問題。在國家加強宏觀調控和證券市場多年熊市的背景下,包括“金新信托”、“慶泰信托”在內的幾家投資證券較多的公司先后發生了業務操作問題,比如資金鏈斷裂、坐莊失敗、挪用信托資金、不能按時兌付等等。2006年12月28日,銀監會公布了《信托公司管理辦法》,2007年3月1日起施行,自此,我國信托業才逐步走向法制化、規范化的發展軌道。
近些年來,信托伴隨著銀行理財迅猛壯大,信托管理的資產中2/3來自于銀行理財產品對接,只有1/3才是真正的集合信托。這么看,信托發展早已畸形了,對應于實體經濟蘊含的金融危機,影子銀行風險中信托最甚。
從影子銀行的資金需求方來看,信托為了盈利,主要為非政策導向行業或領域融資,比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、過剩產能行業與房地產開發商占據較大比重。從信托資金投向構成來看,截至2013年三季度末,投向基礎產業與房地產的資金占比為35.3%,金額達到3.38萬億元,較上年同期增長63.29%。投到工商企業的資金占比29.49%,此類工商企業類似于房地產信托資金,主要用于規避房地產信托融資的種種限制。也就是說,如果再考慮信托貸款、企業債券融資等渠道,投向房地產、基礎產業的資金規模會更大,所對應的金融風險迅速向銀行表外擴張。
信托的主要問題在于,信托一經成立,信托財產享有法律上的獨立性,因此信托制度天生具備SPV(特殊目的載體)的破產隔離功能,但是這一核心與本質功能在現實中并沒有實現。
因此在當前利率市場化與金融脫媒的大環境下,信托與商業銀行一樣面臨轉型。
首先,信托采取了SPV表外融資的形式,淪為銀行通道。信托融資并不是真正的結構化融資,大部分只是為銀行或者其他公司提供通道類的被動管理信托,信托基本上淪為銀行回避監管的業務中(比如同業業務)將資產轉移表外的通道,沒有發揮自身的價值。券商及基金子公司的資管計劃,也常常作為銀行的非標通道,但在吸引客戶時,就算借助人力優勢展開更多的項目調查,也沒辦法和借助信托獨有的“破產隔離”手段的信托公司相比。按理說,如果發生兌付危機,信托公司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,而不是依靠政府或者銀行信用實現“剛性兌付”。依據現在資產證券化風險自留原則,銀行除了對5%不出表部分負責外,對95%出表的部分在信托幫助下理應“破產隔離”。但正如近期中誠信托面臨的兌付危機進展所顯示的,信托公司始終認為自己僅僅為“通道角色”,投資人還是會去找銀行,“破產隔離”名存實亡。從這個角度來看,信托只是在銀行受到信貸控制的情況下,以比銀行更為寬松的信貸標準發放了風險更高的貸款而已,而且由于法規的不同,信托可以實現監管套利。
其次,信托隱含的剛性兌付,改變了信托直接融資的本性。從金融本質的角度來看,變成了與信托先融資,再自己發放貸款給融資方的這種間接金融方式。而正規的資產管理行業,如基金公司的產品,必須要在產品說明書中明確提示產品是不提供保本保收益的特性。信托剛性兌付,使得投資者忽視了投資風險,忽略了對基礎資產的選擇,而將信心完全寄托在信托身上。信托有意無意地強調自身的剛性兌付(這在證券業是違法違規的),并且享受因此而帶來的產品銷售上的便利,迅速占領了市場。目前信托業之所以能夠在非標類的資產管理方面要勝過證券公司,不是因為信托業有更高的風險管理能力或更強的從業人員素質,最根本的還是剛性兌付。
再次,信托做了很多所謂的金融創新,大多是基于制度套利,即鉆制度的漏洞。這種套利無益于改善市場效率,還會使宏觀經濟政策效果大打折扣。而且為發行人增加成本,同時將投資人的錢以影子存款的利率吸引到高風險業務上。這不禁讓人要問一句:金融的實質是什么?金融市場如果只是充當資源向少數人集中(服務于高凈值客戶)、富者更富、貧者更貧甚至劫貧濟富的工具,短期利益大于長期利益、繞過監管制度、整體套政府銀行信用甚至就是監管制度本身的利,就會從根本上忽視金融市場的政治本質和剩余價值的集體屬性。銀行借助信托渠道的表外業務擴張,會計上出了銀行的資產負債表,但只不過是拿監管和會計制度記法來掩耳盜鈴,風險并未出銀行的資產負債表,真正兜底和出資的還是銀行。未來風險暴露,不但會影響信托公司,而且還會牽連整個金融市場特別是直接金融市場。
最后,信托產品的高收益相當于為整個社會的金融產品確定了一個很高的“無風險利率”。信托業、房地產與地方融資平臺一道,對實體經濟形成了擠出效應。也就是說信托公司為金融市場提供了一個虛幻的“無風險產品”,這一產品的無風險性目前被投資者普遍認可,且具備高收益,這實際上將經濟中的無風險利率提高到了信托產品的收益率水平(目前大約在9%-10%,實體企業融資只能在此基準上加上風險溢價)。這對實體經濟的擠壓相當于連續多次加息造成的后果。利率的不斷攀升,使得實體經濟中大部分企業的盈利與現金流都不能覆蓋利息,只能通過發新債還舊債不斷延期、展期,經濟進入所謂的龐氏融資狀態。而一旦風險真正暴露,信托公司本身資本金實力薄弱,再加上沒有類似銀行的撥備覆蓋、存款準備金等限制,信托業實際上根本就沒有剛性兌付和應對危機的能力。
由于信托自身所具有的獨立性,信托是天生的SPV。在我國當前法律框架下,只有信托型SPV能實現資產證券化資產轉移的無爭議性,未來信托應該實現破產隔離這個在信托制度中最核心的競爭優勢。在利率市場化和銀行管理資產負債表的壓力下,圍繞這個制度優勢,信托作為證券化交易結構的核心,可以推動實現真正的“資產證券化”。在金融市場化與資本市場需求下,回歸業務本原,信托公司足以應對泛資產管理時代的激烈競爭。我們始終要明白當前信托幫助銀行搞大量表外業務,始終不能實現證券化產品合法地與銀行其他債務分離,降低資產和負債的期限錯配風險、增強流動性、信用增進、降低成本、幫助投資人分散風險等最重要的功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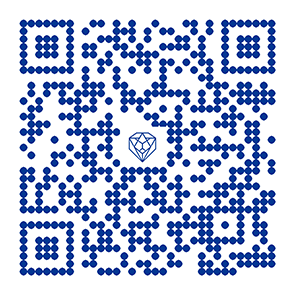





 合格投資者提示
合格投資者提示